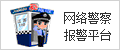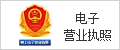简介: 现在我国的能源消费出现了一个转折,从较高的经济增长开始转向平稳增长阶段,这是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产能三个方面来判断的。
记者:您认为雾霾天气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跟煤炭和燃油有何关系?
潘家华:雾霾的形成绝对是跟化石能源的消费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没有任何质疑的。但为什么雾霾突然间变得这么严重,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能源消费的历史。1980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也就只有6.5亿吨标煤,经过二十年后,2000年我们的能源消费总量翻了一番是13.5亿吨标煤。但进入21世纪后,我们能源消费总量保持了非常快速的增长,到现在已经超过了35亿吨标煤。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能源消费结构,化石能源占比是91%,其中煤炭是68%左右,石油在19%左右,天然气是4%左右。其中煤炭的燃烧排放量最大,市场成本低,但社会和环境成本高。从我们能源发展阶段和消费结构来看,中国能源消费单位热值的常规污染物和碳的排放量要远高于以石油为主的发达国家。
但排放并不意味着雾霾必然会生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排放相对集中。
在瑷珲——腾冲(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线以东地区,人口占94%,国土面积占比在40%以下,人口和产业高度密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气候条件。中国东南部区域属于季风气候,海洋的湿润气团往北移动,北部的冷空气向南移动,南北气团容易达到均衡状态,就导致了没有风的稳定气层,不利于污染物扩散。此外我们的技术、标准、监管上都存在一些问题,这样综合的因素导致了雾霾天气的形成。
“能源效率低是个表象伪命题”
记者:现在普遍认为我国的能源效率比较低,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为什么会这样?
潘家华:我认为能源效率低是一个伪命题。中国的能源效率并不低,相对于发展阶段,甚至比发达国家也不低。以炼钢为例,我们现在吨钢的能耗比OECD的平均水平要低,而且我们是从铁矿石炼出来的,而国外废钢占比则较大。我们的煤电,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煤耗在280克/千瓦时左右,这比美国、德国的还要高效。此外,我们汽车的燃油效率也高于美国。必须看到,我们单位面积的建筑能耗也是低于欧洲美国的,尽管我们的舒适程度没有他们高。综合来看,我们不能简单说:中国能源效率低。
但为什么我们单位产值的能耗比较高?分析来看,一是我们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本身的特点就是能耗高。二是我们的产品结构,产品的附加值偏低。比如瑞士的钟表可以卖到几万块钱,而我们制造的手表却很便宜。三是与我们整体的发展水平有关,生产能耗高,生活消费能耗少。四是一些比价因素。例如理发、出租车,同样的服务,同样的能耗,用美元计,单位产值的能耗,中国比美国高出3~5倍,甚至更高,这不能说中国能效低。
如果进行对比就是比技术效率,可以发现中国在世界上并不落后,在许多领域甚至处于领先地位,比如说我们的单晶硅竞争力就很强。
记者:我国能源消耗的强度正在明显下降,近几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也已明显低于1,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和能源消费正进入新的阶段?
潘家华:我认为现在我国的能源消费出现了一个转折,从较高的经济增长开始转向平稳增长阶段,这是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产能三个方面来判断的。一是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看。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像北京、上海及部分沿海地区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这意味着我们工业扩张的空间已经不大,能源消费的增长将不会来自于原材料产业或常规制造业的扩张。相反,由于技术进步,工业制造业的能效会不断提高,能耗会呈下降趋势。
比如德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从1980年至今一直是在下降的,从3.5亿吨标油下降到3.1亿吨标油,总量一直是往下走的。
第二,从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来看。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比一般在70%左右,而我们现在第三产业占比只有46%。我们的第三产业正在提升,以及第二产业相对下降,能源消耗的强度也在下降。未来第三产业对能源的要求也将更多倾向于质,而不是量。
第三,从我们的产能来看。我们的粗钢2013年是7.8亿吨的产量,占世界的48%。有人戏称世界钢铁生产是“中国第一、河北第二、美国第三”,我们的钢铁产能达到10亿吨。如果进一步扩张,市场在哪里?再比如说2013年我们生产了14.56亿部手机,超过了我们的人口总数,汽车生产了2212万辆,彩电1.28亿台。市场空间已经饱和,简单重复的产能扩张就没有空间。
“民资进入有助于减少市场风险和国家投入”
记者: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能源市场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市场化程度明显滞后,请您分析其中原因。
潘家华:能源的特点决定它具有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和战略性地位,国家行政干预控制的成分比较多,基本上属于没有放开市场的领域,多数都由央企直接掌管。比如石油领域,都是由“三桶油”来掌握,民营企业没有空间。说让市场配置资源,但计划经济的色彩仍然十分浓厚,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既定的利益格局。如果不打破这种制度格局,那么让市场配置资源的可能性就没有。以美国页岩气为例,参与开发的都是众多的私营企业,所以就形成一次革命。
现在我们的地方政府与央企打交道是没有风险的,在政治上是对的,这就导致投资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盲目性。政府在改革中应当是一种宏观的调控,而不应进行微观的干预。
比如说阶梯电价、阶梯水价,价格提高后的收益应当补贴给社会,或者用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而不是给企业。另外阶梯差价对富人来讲,经济上的影响也并不明显,进行制度设计,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实际上,非国有部门的参与,不仅有助于减少市场风险,而且有利于减少国家投入。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三峡水电建设的时候,资金上比较紧张。当时我们参与这些方面的一些评估工作,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让移民的生产资料、土地以股份的形式入股,实现利益的一体化,这样就会减少很多阻力。但是,当时的体制不允许这样。
另外,从我们目前对央企的考评体制来看,负责人的政治风险是高于市场风险的。未来的改革应该将两者剥离开,让市场风险高于政治风险,并加大第三方监督制度的建设。
记者:三中全会还提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完善国资管理体制,您对能源行业制度改革有怎样的评价和期许?
潘家华:能源市场的改革严重滞后。首先产权的界定就很不清楚。比如说煤矿是国有的,跟当地老百姓没关系,最后煤矿变成了企业的。产权可以分为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我们的所有权不能变,但收益权和使用权可以调整,更多分配给老百姓,目前是三种权都在国企手里。
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健全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并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这都给能源改革提供了支撑。
第二是投资对市场放开的问题。现在能源领域的投资主要是央企、国企进行的,对民营企业不开放,民资就没有可能来参与竞争。
第三是价格体系。作为政府要站在全社会的高度确保全民享有能源的普遍服务,制止奢侈浪费行为,保护基本价格,放开其他的价格。市场会让价格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并促进就业、消费方式的改变等。
比如瑞士有这样一个制度,对汽油消费征收碳税。这部分税征收上来之后再平均返还给全体人民,消费能源多的人交的税也多,这很值得我们学习。
“碳交易要先建基础设施”
记者:您是研究碳减排方面的专家,对碳减排市场化方面您有怎样的看法?
潘家华:应该说我们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但似乎发展的路径不对。建立碳市场是很好的,但目前我们在认定、报告、核查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就开始搞交易,就好比买汽车,发了牌照,但没有铺公路一样。
对于建立碳交易市场,首先对碳要有非常明确的界定,碳是个什么东西?由谁来界定?还要建立完善的报告核查体系,要建立统一的标准。第三,交易的时候要尽量减少交易成本,比如说英国对于碳税是使用电量进行计算的,核算比较简单方便。此外,我们的碳交易应该进行零碳能源的补贴及生态环境的保护,比如风能、太阳能及生物质能,形成交叉补贴的体系。
记者:全球范围内,您观察能源行业在生产消费观念和技术上正发生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变革或创新?
潘家华:我觉得是可再生能源的高速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价格下降的速度。我记得10年以前,每千瓦太阳能光伏的发电成本是4万多块钱,现在已经降到了万元以内,上网电价只有9毛钱,下降的速度非常快。因此讲可再生能源的前景是无限的,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